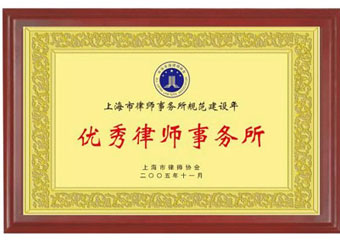普通法或許是英國判例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司法機(jī)關(guān)的有力工具。它使法律保持靈活性并永遠(yuǎn)適用于現(xiàn)代不斷變化的世界。正如桑德拉·弗雷德曼 (Sandra Fredman) 所說,它旨在“防止因法定制度而導(dǎo)致的貧困”。然而,判例法的先例和法官的明智解釋仍然必須以議會法為基礎(chǔ)進(jìn)行補充。因此,有時必須依賴成文法來提供普通法可以應(yīng)用其解釋利益的大綱。1981 年的《刑事未遂法》“試圖”做到這一點。其目標(biāo)是制定某種形式的成文法,以指導(dǎo)和澄清、標(biāo)準(zhǔn)化并在缺乏一致性的情況下提供一定程度的法律確定性。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揭示《刑事未遂法》帶來的改進(jìn),但我也會揭露該法目前的缺陷和改進(jìn)策略。我將主要關(guān)注這樣一個事實,即法律在某些領(lǐng)域的嘗試似乎過于狹窄,而在其他領(lǐng)域則過于寬泛。我還將評估改革是否必要以及哪些選擇最有利的問題。
通過《1981 年未遂犯罪法》改善不可能性
普通法下出現(xiàn)了幾個問題,例如不可能、犯罪行為的術(shù)語不明確以及犯罪意圖要求的不確定性。在 1981 年之前,普通法不承認(rèn)不可能的罪行仍然可以導(dǎo)致被告被定罪的事實。這可以在 Anderton v Ryan 一案中看到,法院的口述提到了“客觀無辜的行為”,即使存在行為和意圖,也不能將其轉(zhuǎn)化為犯罪。這涉及被告,他被控以錄像機(jī)的形式處理被盜財產(chǎn)。她認(rèn)為它是被盜的,但法庭無法證明這一點。因此,法院裁定,在普通法中,如果某人實施犯罪行為,意圖實施他認(rèn)為可能(但實際上不可能)的特定犯罪,則不應(yīng)被定罪。奇怪的是,雖然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得到了滿足,但僅僅因為無法證明所處理的物品被盜,就沒有犯罪。當(dāng)時有很多人擔(dān)心,這會導(dǎo)致邏輯錯誤的延續(xù),并導(dǎo)致進(jìn)一步的案件在這種不可能的基礎(chǔ)上做出決定。

正是由于這種不足,法律委員會才決定頒布《刑事未遂法》。該法案明確規(guī)定,“即使事實表明不可能實施犯罪”,被告仍可被定罪。這在未來的判例法中得到了肯定,而安德頓在 Shivpuri 的毒品走私案中迅速被推翻。在這里,一名男子對他的毒品走私定罪提出上訴,聲稱由于他認(rèn)為是毒品的物質(zhì)實際上不是那種物質(zhì),所以他實際上不能在法律上有罪。法院引用了新的法規(guī),并推理出所有必要的行為不僅僅是為犯罪行為做準(zhǔn)備,而被告人這樣做是為了犯罪。這與第 1(3)(b) 條確認(rèn)為“如果案件事實如他所相信的那樣,他的意圖會被如此看待。” 在 Shivpuri 的情況下,這被稱為物理上的不可能。這意味著不能實施犯罪,因為這些要素并不等同于犯罪。這與法律上的不可能和無能的不可能形成對比。無能是指被告人使用的手段使犯罪不足以產(chǎn)生預(yù)期結(jié)果的案件。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在受害者的食物中放入太少的毒藥或錯誤類型的過敏原。雖然通常手段就足夠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的無能導(dǎo)致了不可能。在 Taaffe 案中,被告錯誤地認(rèn)為進(jìn)口貨幣是非法的,這是法律上不可能的最好例證。盡管他有意圖并且正在實施犯罪行為,但他被判無罪。這是因為進(jìn)口貨幣的犯罪并不違法,必須有違法犯罪的行為才能被定罪。Haughton 和 Smith 是物理上和法律上不可能的一個例子。在這里,贓物被警察沒收,然后一名臥底警察假裝將它們交給第三方,然后第三方被指控處理贓物。這不僅是物理上的不可能,因為不可能處理贓物,而且處理未被盜的貨物在法律上也不是犯罪。在 Taaffe 案中,被告錯誤地認(rèn)為進(jìn)口貨幣是非法的,這是法律上不可能的最好例證。盡管他有意圖并且正在實施犯罪行為,但他被判無罪。這是因為進(jìn)口貨幣的犯罪并不違法,必須有違法犯罪的行為才能被定罪。Haughton 和 Smith 是物理上和法律上不可能的一個例子。在這里,贓物被警察沒收,然后一名臥底警察假裝將它們交給第三方,然后第三方被指控處理贓物。這不僅是物理上的不可能,因為不可能處理贓物,而且處理未被盜的貨物在法律上也不是犯罪。在 Taaffe 案中,被告錯誤地認(rèn)為進(jìn)口貨幣是非法的,這是法律上不可能的最好例證。盡管他有意圖并且正在實施犯罪行為,但他被判無罪。這是因為進(jìn)口貨幣的犯罪并不違法,必須有違法犯罪的行為才能被定罪。Haughton 和 Smith 是物理上和法律上不可能的一個例子。在這里,贓物被警察沒收,然后一名臥底警察假裝將它們交給第三方,然后第三方被指控處理贓物。這不僅是物理上的不可能,因為不可能處理贓物,而且處理未被盜的貨物在法律上也不是犯罪。
通過 1981 年未遂犯罪法改進(jìn) Actus Reus
在《刑事未遂罪法》出臺之前,圍繞著在被告的行為中究竟需要證明什么才能定罪,存在著大量的謎團(tuán)。事實證明,這種不穩(wěn)定和不健全對辯方和控方都是潛在的危險。普通法通過先例表明,“最后行為”是對未遂責(zé)任的最準(zhǔn)確測試。因此,只有那些被認(rèn)為接近成功完成的行動才會被起訴。即使在立法機(jī)構(gòu)頒布之后,普通法仍堅持將“不僅僅是準(zhǔn)備”一詞解釋為危險地接近已完成的行為本身。這產(chǎn)生了關(guān)于被告是否真的超越了其法律允許的界限的證據(jù)問題。在 Gullefer 的情況就是這樣,一名男子跳上賽馬場,希望分散狗的注意力,這樣比賽就會被沒收并退還他的錢。法院奇怪地裁定,這并沒有超出準(zhǔn)備階段,因為他沒有與簿記員對質(zhì),因此還沒有達(dá)到可定罪的階段。當(dāng)然,這種邏輯暗示了在該法案建立甚至不僅僅是準(zhǔn)備的松散指導(dǎo)之前,法律中普遍存在的危險和問題。然而,這種對對抗的依賴以及準(zhǔn)備和執(zhí)行之間的模糊界限正是該法案所尋求改善的。法院奇怪地裁定,這并沒有超出準(zhǔn)備階段,因為他沒有與簿記員對質(zhì),因此還沒有達(dá)到可定罪的階段。當(dāng)然,這種邏輯暗示了在該法案建立甚至不僅僅是準(zhǔn)備的松散指導(dǎo)之前,法律中普遍存在的危險和問題。然而,這種對對抗的依賴以及準(zhǔn)備和執(zhí)行之間的模糊界限正是該法案所尋求改善的。法院奇怪地裁定,這并沒有超出準(zhǔn)備階段,因為他沒有與簿記員對質(zhì),因此還沒有達(dá)到可定罪的階段。當(dāng)然,這種邏輯暗示了在該法案建立甚至不僅僅是準(zhǔn)備的松散指導(dǎo)之前,法律中普遍存在的危險和問題。然而,這種對對抗的依賴以及準(zhǔn)備和執(zhí)行之間的模糊界限正是該法案試圖改善的地方。
據(jù)說,該法規(guī)將焦點轉(zhuǎn)移到了不只是準(zhǔn)備/計劃的行為上,擴(kuò)大了先前的“最后行為”或“最終行為”的范圍。這是對瓊斯案的判決的序幕和強化,在判決中,法院稱“不僅僅是準(zhǔn)備”具有其常規(guī)含義,絕不暗示“最后一幕”。在本案中,被告被判有罪,因為他將槍指向受害者,并且無需證明他仍需要進(jìn)行后續(xù)動作,例如拔槍、瞄準(zhǔn)和扣動扳機(jī)。這完全符合主觀主義的觀點,即沒有必要等到犯罪總是接近實施時才懲罰它。
普通法似乎也為放棄的辯護(hù)打開了一個窗口。在坎貝爾提起了這樣一個案件,警方發(fā)現(xiàn)一名男子帶著搶劫所需的工具在郵局附近游蕩。被捕并定罪后,他的被告聲稱他曾打算搶劫銀行,但已重新考慮。這種悔改和不執(zhí)行的想法受到法庭的歡迎,因此他們認(rèn)定他無罪,因為他沒有能力犯罪。《犯罪未遂法》的部分目標(biāo)是使這種客觀主義思想過時,并使明顯意圖和即將執(zhí)行的犯罪更加早期。意義,法規(guī)將試圖推翻這樣的決定,使之成為更接近 Toothill 的場景,竊賊在試圖進(jìn)入受害者家時被捕,法院認(rèn)定他作為侵入者進(jìn)入并按門鈴構(gòu)成在一定程度上執(zhí)行他的計劃。起訴。這似乎更符合執(zhí)行計劃的“實質(zhì)性步驟”的想法,并且似乎更具包容性,但與該法案巧妙地試圖達(dá)到的主觀主義者提議的“第一步”步驟并不完全一致。
通過 1981 年未遂犯罪法改善犯罪意圖
在《未遂犯罪法》出臺之前,普通法對未遂行為的犯罪意圖要求并不確定。有關(guān)于心理因素必須有多嚴(yán)格的問題。在制定該法規(guī)之前,犯罪意圖要求非常高,并且只有意圖被視為必不可少的。在 Mohan 中發(fā)現(xiàn),只有特定的意圖才能被發(fā)現(xiàn),魯莽的心態(tài)是不夠的。法院認(rèn)為,即使被告在接近警察時加快了駕駛速度,但必須表明他想要造成嚴(yán)重的身體傷害,而不僅僅是他意識到他可以并且不顧后果是否會這樣做。如此高標(biāo)準(zhǔn)的心理預(yù)謀在汗案中被推翻,法院駁回了被告對其強奸未遂定罪的抗辯。法院裁定,強奸未遂和強奸的犯罪意圖必須一致,因此性交的意圖和對受害者是否同意的魯莽行為足以證明定罪是合理的。1992 年總檢察長參考文獻(xiàn)第 3 號證實了這種說法,其中發(fā)現(xiàn),在預(yù)期的財產(chǎn)損失過程中是否會危及生命的魯莽行為是有效的,因為它符合已完成的罪行。因此規(guī)定,要確定犯罪未遂的心理條件,必須考察完整犯罪的心理要素。法院裁定,強奸未遂和強奸的犯罪意圖必須一致,因此性交的意圖和對受害者是否同意的魯莽行為足以證明定罪是合理的。1992 年總檢察長參考文獻(xiàn)第 3 號證實了這種說法,其中發(fā)現(xiàn),在預(yù)期的財產(chǎn)損失過程中是否會危及生命的魯莽行為是有效的,因為它符合已完成的罪行。因此規(guī)定,要確定犯罪未遂的心理條件,必須考察完整犯罪的心理要素。法院裁定,強奸未遂和強奸的犯罪意圖必須一致,因此性交的意圖和對受害者是否同意的魯莽行為足以證明定罪是合理的。1992 年總檢察長參考文獻(xiàn)第 3 號證實了這種說法,其中發(fā)現(xiàn),在預(yù)期的財產(chǎn)損失過程中是否會危及生命的魯莽行為是有效的,因為它符合已完成的罪行。因此規(guī)定,要確定犯罪未遂的心理條件,必須考察完整犯罪的心理要素。1992 年總檢察長參考文獻(xiàn)第 3 號證實了這種說法,其中發(fā)現(xiàn),在預(yù)期的財產(chǎn)損失過程中是否會危及生命的魯莽行為是有效的,因為它符合已完成的罪行。因此規(guī)定,要確定犯罪未遂的心理條件,必須考察完整犯罪的心理要素。1992 年總檢察長參考文獻(xiàn)第 3 號證實了這種說法,其中發(fā)現(xiàn),在預(yù)期的財產(chǎn)損失過程中是否會危及生命的魯莽行為是有效的,因為它符合已完成的罪行。因此規(guī)定,要確定犯罪未遂的心理條件,必須考察完整犯罪的心理要素。
1981 年刑事未遂法令目前存在的問題
基于客觀主義觀點和普通法解釋的決定表明,大多數(shù)嘗試,尤其是那些具有暴力性質(zhì)的嘗試,必須涉及一定程度的對抗。否則,舉證責(zé)任將被證明是控方無法承受的負(fù)擔(dān)。這種對抗理論的不公正體現(xiàn)在 Geddes 等案例中,在該案例中,一名男子被發(fā)現(xiàn)帶著他收集的所有必需品藏在廁所里,等待他可以錯誤地監(jiān)禁一個孩子。法院裁定,由于這只是簡單的準(zhǔn)備,因此不符合“不僅僅是準(zhǔn)備”的條件,并且被視為尚未實施該計劃。這種推理似乎很荒謬,因為被告必須觸摸兒童才能被定罪似乎不太可能。他進(jìn)入大樓的事實不僅表明學(xué)校方面缺乏安全性令人擔(dān)憂,而且還故意靠近,這超出了他在自己家中進(jìn)行的準(zhǔn)備工作。正是這種對抗的想法困擾著該法案下的現(xiàn)行法律,應(yīng)該廢除。如果“不僅僅是準(zhǔn)備”允許犯罪分子潛伏在附近有孩子的浴室并且不受懲罰,那么就需要另一種選擇犯罪行為的術(shù)語。
現(xiàn)行法律中的另一個潛在問題是,有條件的企圖,即被告人基于出現(xiàn)的某些情況打算犯罪的企圖,過于依賴于起訴書的結(jié)構(gòu)。例如,如果一個人闖入汽車偷錢包,但在發(fā)現(xiàn)錢包里沒有錢包后離開了房屋,那么他很可能不會因搶劫/盜竊未遂而被定罪。這一切都取決于起訴書是如何寫的。因此,如果控方說指控是“試圖從錢包里偷錢”,那么犯罪分子將有更好的機(jī)會被無罪釋放,而不是因為沒有錢而被指控為“試圖偷走錢包里的東西”存在于錢包中。
法律委員會本身也感嘆“不僅僅是準(zhǔn)備”的測試過于模糊和不確定,導(dǎo)致陪審團(tuán)對在哪里劃定決定性的分界線感到困惑。
委員會關(guān)注公平標(biāo)記的想法,以及是否應(yīng)該將即將嘗試但重新考慮的人與成功嘗試但未能真正執(zhí)行和實施犯罪的人放在同一類別中。正如約翰史密斯爵士所說,法律熱衷于關(guān)注犯罪所涉及的傷害:“有罪取決于行為是否導(dǎo)致有害結(jié)果的想法,盡管它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在我們的法律中根深蒂固。” 歸根結(jié)底,企圖謀殺并重新考慮的人,企圖謀殺但未能謀殺的人,以及成功謀殺的人,在人們眼中是不同的,因此應(yīng)在法律上加以區(qū)分。進(jìn)一步證明“不僅僅是準(zhǔn)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它既適用于可能的嘗試,也適用于不可能的嘗試。因此,該短語的解釋并不意味著面對或接近最后的行為,因為這在實際或邏輯上不適用于不可能的情況。
1981 年現(xiàn)行刑事未遂法令的進(jìn)一步改革
法律委員會最近發(fā)布了他們的建議,以改善上述困難和歧義。他們擔(dān)心現(xiàn)行法律在準(zhǔn)備案件中過于狹隘的務(wù)實問題(正如 Geddes 所見證的那樣),并希望使法律更加包容所有有罪方。他們的想法涉及將未遂罪分為兩種不同的罪行。第一次犯罪將是犯罪準(zhǔn)備,包括被告在執(zhí)行過程中“在工作中所做”的那些行為。第二次犯罪將是犯罪未遂,這將根據(jù)最后一次行為進(jìn)行更明確的定義。這兩項新罪行都將受到相同的最高刑罰,并且該行為是否為最后行為的測試將作為法律問題交由法庭處理。
克拉克森堅決反對該提議,并在其文章中的幾個重點中闡明了這一點。首先,他說“未遂罪”的創(chuàng)建過于接近“最后一幕”的想法,因此過于狹隘,使瓊斯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其次,他認(rèn)為準(zhǔn)備罪可能導(dǎo)致過度刑事定罪,因為它可能會過早地攻擊準(zhǔn)備并導(dǎo)致思想犯罪。這不僅會因越來越多的案件而堵塞司法系統(tǒng),而且還會將責(zé)任擴(kuò)大到超出議會預(yù)期的范圍。另一個會給法院增加大量不必要負(fù)擔(dān)的考慮是,兩種企圖之間仍然沒有足夠明確的區(qū)別,這將導(dǎo)致需要解釋性判例法。第四,他指出,法律委員會沒有討論準(zhǔn)備嘗試不可能的責(zé)任的區(qū)別,也沒有區(qū)分準(zhǔn)備和嘗試的處罰。這冒著陪審團(tuán)選擇對準(zhǔn)備定罪的風(fēng)險,因為區(qū)別并不清晰,而且似乎是一種稍微不那么冒犯性的犯罪。除了沒有反映所犯的真實罪行外,這是一個錯誤的公平標(biāo)簽案例,是不可接受的。最后,法律對那些重新考慮自己行為的人沒有同情心。Ashworth 指出,一個人離完全犯罪越遠(yuǎn),就越不可能將未完成僅僅歸因于道德運氣。
克拉克森接著說,雖然現(xiàn)行法律需要改革,但最好的方法是制定一個新的未遂法定定義,并以一系列例子為后盾,表明新測試應(yīng)涵蓋的行為類型. 他想采用客觀主義的觀點,即被告已經(jīng)跨越了道德門檻(越過盧比孔河),并表現(xiàn)出類似于完全犯罪的道德責(zé)任。然而,他想考慮到危險行為包含在犯罪意圖中的事實,那些有危險意圖的人應(yīng)該承擔(dān)責(zé)任。因此,他認(rèn)為,只要有行為證實了這方面的危險,企圖者就成為被告。他建議,門檻應(yīng)該是正在實施的相關(guān)犯罪的“活生生的危險”之一。然而,這似乎仍然沒有達(dá)到阻止企圖和阻止他們的委托所必需的寬度。雖然措辭肯定會澄清Geddes的惡法,但像Gullefer這樣的案件仍然籠罩著不確定性。也許更好的方法會涉及 L Turner 所說的“明確涉及特定犯罪的實施”。這樣的措辭選擇肯定會確保(正如“明確”這個詞所暗示的那樣)幾乎不會懷疑被告將要嘗試什么,并且不會混淆“危險”一詞的上下文,因為某些罪行可能是非法的,但不一定危險(走私毒品)。似乎以某種方式達(dá)不到阻止企圖和阻止他們的委托所必需的寬度。雖然措辭肯定會澄清Geddes的惡法,但像Gullefer這樣的案件仍然籠罩著不確定性。也許更好的方法會涉及 L Turner 所說的“明確涉及特定犯罪的實施”。這樣的措辭選擇肯定會確保(正如“明確”這個詞所暗示的那樣)幾乎不會懷疑被告將要嘗試什么,并且不會混淆“危險”一詞的上下文,因為某些罪行可能是非法的,但不一定危險(走私毒品)。似乎以某種方式達(dá)不到阻止企圖和阻止他們的委托所必需的寬度。雖然措辭肯定會澄清Geddes的惡法,但像Gullefer這樣的案件仍然籠罩著不確定性。也許更好的方法會涉及 L Turner 所說的“明確涉及特定犯罪的實施”。這樣的措辭選擇肯定會確保(正如“明確”這個詞所暗示的那樣)幾乎不會懷疑被告將要嘗試什么,并且不會混淆“危險”一詞的上下文,因為某些罪行可能是非法的,但不一定危險(走私毒品)。像 Gullefer 這樣的案例仍然具有不確定性。也許更好的方法會涉及 L Turner 所說的“明確涉及特定犯罪的實施”。這樣的措辭選擇肯定會確保(正如“明確”這個詞所暗示的那樣)幾乎不會懷疑被告將要嘗試什么,并且不會混淆“危險”一詞的上下文,因為某些罪行可能是非法的,但不一定危險(走私毒品)。像 Gullefer 這樣的案例仍然具有不確定性。也許更好的方法會涉及 L Turner 所說的“明確涉及特定犯罪的實施”。這樣的措辭選擇肯定會確保(正如“明確”這個詞所暗示的那樣)幾乎不會懷疑被告將要嘗試什么,并且不會混淆“危險”一詞的上下文,因為某些罪行可能是非法的,但不一定危險(走私毒品)。
盡管普通法的發(fā)展在本質(zhì)上是有益的,但將成文法添加到未遂法律領(lǐng)域既具有啟發(fā)性又是必要的。糾正了若干缺陷,顯著擴(kuò)大了責(zé)任范圍。盡管引入了 1981 年《未遂未遂犯罪法》,但現(xiàn)行的未遂犯罪法仍需修訂。在犯罪未遂罪中,應(yīng)盡早對那些行為接近于完全犯罪并表現(xiàn)出與完全犯罪相當(dāng)?shù)牡赖逻^錯程度的人施加責(zé)任。重新制定的定義會比法律委員會的改革建議有效得多。這個修改后的定義需要擺脫被告應(yīng)該以對抗方式開始犯罪的觀念。這一新定義必須得到一份明確的構(gòu)成企圖的行為示例清單的支持,并且對該定義的解釋成為法律問題。只有通過澄清和一致性,關(guān)于未遂罪的法律才能反映被告的可責(zé)性和定罪的適當(dāng)階段。 深圳律師事務(w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