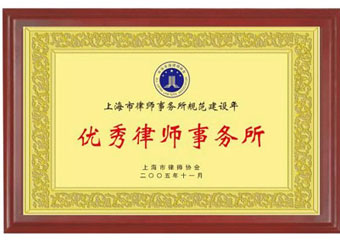我國刑法第271條規(guī)定,公司、企業(yè)或許其它單位的職員,應(yīng)用職務(wù)上的方便,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shù)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許拘役;數(shù)額偉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能夠并處沒收財產(chǎn)。今天深圳刑事律師就來講一講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界限與競合。

職務(wù)侵占罪的組成要件是:
1.本罪侵占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quán)。侵占的對象必須是行為人所在單位的合法財物。
2.主觀方面表現(xiàn)為應(yīng)用職務(wù)上的方便,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shù)額較大的行動。
3.犯法主體為非法主體,及公司、企業(yè)或許其它單位的職員才能構(gòu)成,而且這些人員不屬于從事公務(wù)的國家工作人員。
4.主觀方面由有意組成,且有意內(nèi)容具有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
刑法第382條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根據(jù)刑法第383條規(guī)定,個人貪污數(shù)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chǎn);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chǎn)。第384條規(guī)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wù)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jìn)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shù)額較大、進(jìn)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shù)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jié)嚴(yán)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數(shù)額巨大不退還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根據(jù)相關(guān)司法解釋,挪用公款進(jìn)行營利活動或其他活動的,數(shù)額較大的起點為1萬元至3萬元,作為“情節(jié)嚴(yán)重”情形之一的數(shù)額巨大起點是15萬元至20萬元;挪用公款進(jìn)行非法活動的,5000元至1萬元為追究刑事責(zé)任的起點,5萬元至10萬元以上屬于“情節(jié)嚴(yán)重”的情形之一。可見,對于同樣的數(shù)額,貪污罪的處刑明顯重于挪用公款罪。因而,準(zhǔn)確界定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理論通說認(rèn)為,貪污罪與職務(wù)侵占罪、挪用公款罪與挪用資金罪的主要區(qū)別在于主體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故本文的討論,同樣適用于職務(wù)侵占罪與挪用資金罪之間的關(guān)系
誤區(qū)之一:貪污與挪用的關(guān)鍵區(qū)別在于非法占有目的
理論界眾口一詞地認(rèn)為,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主要、根本或者說關(guān)鍵區(qū)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永久性地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例如,刑法通說教科書指出,“挪用公款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并不存在永久性地占有公款的目的,而只是意圖暫時占有、使用公款,準(zhǔn)備以后歸還;而貪污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卻是為了將公共財物永久性地非法占為己有……挪用公款是否轉(zhuǎn)化為貪污,應(yīng)當(dāng)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具體判斷和認(rèn)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其實,貪污與挪用公款罪的關(guān)鍵區(qū)別并非在于,是出于一時性地“非法占用”,還是永久性地“非法占有”,而是在于,行為人將公款非法置于自己的控制支配下的狀態(tài),是否嚴(yán)重妨礙了單位即公款所有權(quán)人對于公款的利用支配。具體判斷可以參照財產(chǎn)犯罪理論中區(qū)分盜竊罪與不可罰的盜用行為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
盜用即使用盜竊,是指出于暫時使用他人財物之后予以返還的意圖,而破壞他人占有的行為。如基于返還的意思偷開其他汽車兜風(fēng)。[3]關(guān)于偷開汽車,日本判例最初的態(tài)度是,暫時性使用但具有返還的意思的,不成立盜竊罪;反之,若擅自使用之后,具有損壞或者使用后丟棄的意思,則認(rèn)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成立盜竊罪。不過,這一立場以后發(fā)生了改變。對于暫時性地使用他人汽車的案件,判例認(rèn)為,即便具有返還的意思,仍可認(rèn)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成立盜竊罪。此外,對于出于獲取信息的意思,將他人的秘密資料帶出復(fù)印后將原件及時返還原處的案件,日本判例也認(rèn)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對作為有形物的載體本身成立盜竊罪。關(guān)于使用盜竊的可罰性,理論上的分歧在于:(1)認(rèn)為只要取得了占有,就應(yīng)成立奪取罪的見解;(2)認(rèn)為該種侵害占有的行為只要沒有達(dá)到可罰的程度,就不應(yīng)予以處罰的見解;(3)認(rèn)為即便侵害了占有,但只要沒有排除權(quán)利人而像合法占有者一樣進(jìn)行支配的意思,就不成立奪取罪的見解。雖然日本刑法理論上存在上述爭論,但現(xiàn)在多數(shù)說認(rèn)為,即便只是具有暫時性地使用的意思,但若并無事后返還的意思,而是出于使用之后予以丟棄,或者即使存在事后返還的意思,但若出于侵犯相當(dāng)程度的利用可能性的意思,達(dá)到了可罰性程度的法益侵害的危險,以及盡管存在事后返還的意思,但若存在消耗物上價值的利用意思的,都有可能被認(rèn)為并不缺乏排除的意思,而具有了非法占有目的。結(jié)果是,這些情形不再屬于不可罰的盜用行為,而應(yīng)作為盜竊罪處理。
在德國,對于盜用汽車的行為,有返還的意思的,一般否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僅成立盜用交通工具罪,但若在使用后隨意放置,或者使用后丟棄的,則應(yīng)肯定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成立盜竊罪。韓國大法院判例的立場是,擅自使用他人財物時,如果該使用行為引起財物本身含有的經(jīng)濟(jì)價值上的損耗,或者將用完的財物拋棄,以及長時間占有而不及時歸還的,都能夠肯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有成立盜竊罪的余地。
關(guān)于偷開汽車,我國理論通說與司法實踐認(rèn)為,只有盜竊機動車作為犯罪工具使用,以及多次偷開導(dǎo)致機動車喪失的,才有可能成立針對機動車的盜竊罪。即使偷開機動車當(dāng)作犯罪工具使用,只要用后將機動車送回原處或停放到原處附近,車輛未丟失的,都不成立針對機動車的盜竊罪。可以看出,國外立法和判例,對于擅自使用他人的所有物(如盜用汽車)的,造成了財物本身經(jīng)濟(jì)價值上的損耗,或者相當(dāng)程度地排除了所有權(quán)人對于財物的占有使用時,都肯定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可成立盜竊罪。而我國理論與實務(wù)對于一時性地使用他人財物的行為,卻沒有進(jìn)行認(rèn)真的辨析,簡單地以有無返還的意思區(qū)分罪與非罪。
應(yīng)該說,“財物、財產(chǎn)都是權(quán)利人實現(xiàn)經(jīng)濟(jì)目的與社會目的的手段,是被權(quán)利人利用以達(dá)致其目的的工具。所以,所謂對財產(chǎn)的保護(hù),更重要的是對權(quán)利人利用財產(chǎn)的保護(hù);而權(quán)利人對財產(chǎn)的利用,并不只是利用物體本身,更要利用物體的價值。”因而,“一時使用的行為是否具有可罰性,不僅要考慮行為人有無返還的意思、使用時間的長短,更要考慮財物的重大性、對被害人的利用可能性的妨害程度等。”也就是說,不能認(rèn)為因為使用盜竊的行為人具有用后歸還的意思,即不具有永久性地排除他人占有的意思,就認(rèn)為一概不值得作為盜竊罪處罰。而應(yīng)認(rèn)為,“在使用盜竊的情形下,毫無疑問已經(jīng)侵害了對方的占有,至于是否值得刑罰處罰,無非是要考慮使用時間的長短、盜用對象價值的大小、盜用期間內(nèi)是否嚴(yán)重妨礙了物主對于財物的利用。”
同理,對于所謂挪用公物的行為,即便不具有永久性地占為己有的意思,只要公物的價值不菲,挪用行為對公物形成了不可逆轉(zhuǎn)的消耗、磨損,挪用時間較長,以致嚴(yán)重妨礙了所有權(quán)人對于公物的利用的,就完全可能認(rèn)為挪用人具有排除的意思和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應(yīng)以貪污罪或職務(wù)侵占罪定罪處罰。例如,某局局長譚某1998年以單位名義購進(jìn)一輛豪華轎車,卻長期放在家中供其家人使用達(dá)兩年之久。檢察院對其立案偵查發(fā)現(xiàn),他家的電視機、音響、空調(diào)等高檔用品全是從單位“借”的,遂以貪污罪起訴。被告人辯稱這些物品全是向單位“暫借使用”,并都向單位出借了借條,無永久占有之目的,不構(gòu)成貪污罪。因為此案的犯罪對象并非救災(zāi)、搶險等特定款物,也非資金錢款,所以不構(gòu)成挪用特定款物罪和挪用公款罪。此案若按照只要行為人具有用后歸還的意思,就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之通說立場,的確不能評價為侵吞型貪污罪,從而形成明顯的處罰漏洞。這無疑意味著,通說向貪官們指明了一條康莊大道:家中不管缺什么,如汽車、電視機、冰箱、空調(diào)、空氣凈化器、抽水馬桶、全套組合家具乃至房屋,直接用公款以單位名義購買后“借”回家使用便是,就算用個十年、八年,也不用擔(dān)心承擔(dān)挪用公款罪或貪污罪的刑事責(zé)任,相反,若是挪用公款后以個人名義購買上述商品放在家中使用,即便只用三、五個月,也難逃挪用公款罪之刑責(zé)。
公款作為種類物,不同于作為特定物的公物,其占有、使用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民法理論上,為便于作為流通手段的現(xiàn)金的交易順暢進(jìn)行,一般認(rèn)為金錢的占有與所有是一致的。刑法理論一般討論受托保管的金錢的權(quán)利歸屬問題,認(rèn)為對于受托保管的封緘的現(xiàn)金(密封的現(xiàn)金),無論是現(xiàn)金的占有還是所有權(quán),都屬于委托人,故受托人據(jù)為己有的,成立盜竊罪;而對于允許消費的消費寄托(如存入銀行)的現(xiàn)金,則其所有權(quán)及占有權(quán)均轉(zhuǎn)移至受托保管人,受托人使用了該現(xiàn)金的,也不存在侵占的問題。但是,對于限定了用途的受托保管的現(xiàn)金,以及受托催收債務(wù)而來的現(xiàn)金,受托人加以使用的,是否成立侵占罪,在刑法理論上看法并不一致。按照民法上金錢占有即所有的理論,因現(xiàn)金的占有與所有權(quán)都屬于受托保管人,則不存在成立易占有為所有的侵占罪的問題。對此,日本學(xué)者西田典之指出,民事法律之所以認(rèn)為所有與占有一致,是因為對于金錢這種具有極強流通性的交換、結(jié)算手段,為了保護(hù)動態(tài)的交易安全,有必要直接承認(rèn)所有權(quán)的一并轉(zhuǎn)移。然而,刑法不同于民事法律,其保護(hù)的是交易雙方的靜態(tài)權(quán)利關(guān)系。因此,刑法理論通說及判例認(rèn)為,在刑事法律上,與其他動產(chǎn)一樣,受托金錢的所有權(quán)仍然屬于委托人。因此,受托保管限定用途的現(xiàn)金的人擅自使用的,也能成立委托物侵占罪。不過,在受托保管現(xiàn)金,或者受托購買物品而暫時持有他人現(xiàn)金的場合,只要行為人身邊或者家中另外持有等額的現(xiàn)金,或者在銀行擁有相應(yīng)數(shù)額的存款,即便暫時動用了現(xiàn)金,也不會認(rèn)為發(fā)生了對“金額所有權(quán)”的侵害,即不認(rèn)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而不屬于侵占行為,不成立委托物侵占罪。

所謂挪用,其實就是非法使用自己所控制、支配、占有下的他人所有的財物,屬于“使用侵占”。關(guān)于使用侵占,國外刑法理論和判例認(rèn)為,如果該使用行為達(dá)到了不為權(quán)利人所允許的程度、狀態(tài),則可以肯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例如,委托人要求好好保管汽車,受托人卻擅自駕車的,雖然這種行為未必立即構(gòu)成委托物侵占罪,但如果本來只允許短時間使用,卻連續(xù)數(shù)天駕駛受托保管的汽車,完全可能成立委托物侵占罪。又如,受托保管機密資料的人未經(jīng)允許,而將機密資料帶出單位復(fù)印后及時返還原件的,仍可構(gòu)成委托物侵占罪。由此,前述某局局長將單位的豪華轎車、電視機、音響、空調(diào)挪為家用的案件,無疑成立貪污罪,而根本無需討論公物是否屬于挪用公款罪對象之類的問題。
關(guān)于挪用金錢,由于限定了用途的金錢本身的特定性并不是問題,因此,行為人即便另外擁有支票或者其他確實存在的債權(quán),只要不是身邊或者家中存在可以支配的等額的金錢(或者在銀行擁有相應(yīng)數(shù)額的存款),即使行為人存在日后填補虧空的意思與財力,日本多數(shù)學(xué)者及判例仍然認(rèn)為,這種情形下行為人并不缺乏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否認(rèn)委托物侵占罪的成立。也就是說,只是在例外的情況下,根據(jù)所挪用的金額大小,以及所預(yù)想的填補虧空的確定性程度等,而可能排除可罰的違法性或者非法占有目的。

深圳刑事律師總結(jié)到,貪污罪與挪用公款罪的區(qū)別并非在于,是出于用后歸還的意圖,還是基于永久性地非法占有目的,而應(yīng)根據(jù)利用可能性、金額、時間、風(fēng)險、財力等因素進(jìn)行綜合衡量。